两岸合同面面观(一)
一、案例事实
老廖在桃园有一家经营了30年的A成衣公司,专做成衣进出口贸易,和世界知名的几个品牌都有合作经验,在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也有几家固定合作的代工成衣厂。2019年4月份时,老廖收到美国B品牌商的询价电子邮件,双方经过一连串的报价、议价,最终在桃园签订了总价美金(以下同)85万元的订单,订单中包含有不少特殊的规格要求,并且约定了首付款25.5万元、违约金25.5万元。老廖在品牌商来接洽后,便已开始与两岸几家常合作的代工厂洽谈,进行接单的准备。几经寻觅,老廖终于确定由广东东莞一家C成衣厂承接,并且由A公司与C成衣厂在东莞签署了承揽合同。
因为老廖在拟定承揽合同时,疏忽遗漏了B品牌商的订单中一项特殊规格要求,没有将特殊规格的要求约定在合同条款里,导致首批出货就遭到B品牌商在验货后通知退货。老廖在收到B品牌商的通知后,才惊觉是属于自己的疏失,并且积极与B品牌商进行沟通协调,希望能够取得谅解进而通过验收。但是B品牌商为了维持设计水准、也为了自身营收效益考量,最后决定维持退货的决定,并且委托律师于2019年12月份在桃园地院起诉要求解除与A公司的契约关系、A公司应返还已支付价金25.5万元、A公司应给付违约金25.5万元,全案经判决B品牌商胜诉、并于2020年6月份确定。
为了减少损失,老廖在B品牌商表示退货时便与C成衣厂联系告知货品有瑕疵的情况,并要求C成衣厂分担损失1/2,C成衣厂起初因为不知道详情而同意支付1/2的损失、且已经将款项汇付给老廖。孰料C成衣厂嗣后得知退货是因为老廖自己疏忽造成,与C成衣厂根本无关,因此向老廖要求返还支付的款项未果,因而于2020年1月份委托律师在东莞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老廖返还已支付款项人民币170万元,全案经判决C成衣厂胜诉、并于2020年8月份生效。
二、案例相关法律关系解析
合同,是中国大陆的用语,意思与台湾地区使用的契约是一样的,指的都是“双方当事人对于一件交易的各项重要事项达成一致的合意而签订的书面”。在商业实务上,也常会有某公司下订单给某公司购买产品,就如案例中的B品牌商下订单给A成衣公司一般,这样的交易行为中的订单也属于契约或合同。
(一)、当事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B品牌商与A成衣公司间的买卖契约
在本案例中B品牌商与老廖的A成衣公司之间所成立的法律关系,属于买卖契约关系;又因为是跨越二个国家的买卖交易行为,属于国际贸易,因此在法律的适用上也与一般的买卖交易不同。虽然1988年1月1日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契约公约》是在规范跨国买卖交易契约的法律,但是依据该公约的1条的1项的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a)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b)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然而我国并非该公约的缔约国,而且本案例所揭橥的事实内容也并未表述“缔约双方均愿意遵守该公约的相关规定”,是以本案例并不适用该公约。
接下来,本案例在法律关系解构时应当以我国《民法》、《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法律关系解构与适用。因此,依据《民法》第226条规定: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者,债权人得请求赔偿损害(第1项)、前项情形,给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于债权人无利益时,债权人得拒绝该部之给付,请求全部不履行之损害赔偿(第2项);第250条第1项规定:当事人得约定债务人于债务不履行时,应支付违约金;第256条规定:债权人于有第226条之情形时,得解除其契约;第259条第1款规定:契约解除时,当事人双方回复原状之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依左列之规定:一、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
A成衣公司与C成衣厂间的承揽合同
在本案例中,A成衣公司与C成衣厂之间所成立的法律关系,属于《合同法》(旧法,该合同签署地在东莞,原则上适用该法)中的承揽合同关系。依据该法第251条第1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A成衣公司为定作人,C成衣厂为承揽人,因此A成衣公司将订单所需数量的成衣制作工作,依据承揽合同的规定,交付给C成衣厂完成。
此外,依据同法第261条规定: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品质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然而在该合同的约定条款,基本上根源于A成衣公司与B品牌商所签订的买卖订单。但是因为老廖的疏忽,并未将订单中的某项特殊规格要求在承揽合同中完整体现,以致C成衣厂依据承揽合同所制作的成品,不符合B品牌商的规格要求;况且老廖在C成衣厂向老廖交货时,老廖也没有发现自己的疏忽、进而发现成衣不符合规格要求,最终导致退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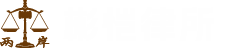



 客服1
客服1 